鄂西的山坳里,稻子黄了又青,青了又黄,可有些事像扎在地里的石桩,多少年过去,碰一碰还是硌得慌。我记事时,村里只有罗家是青砖瓦房,飞檐翘角在一片土坯房里扎眼得很。罗家的独苗罗家中,是我们这些野孩子眼里的怪人——三十好几的人了,总混在孩子堆里抢糖吃,却连谷苗和稗子都分不清,村里老人常对着他的背影啐唾沫:”读了十年书,拉了九年痢,连个’罗’字都写不全!”

他媳妇梁氏总是低着头走路,蓝布褂子洗得发灰,袖口磨出了毛边。我常见她蹲在猪圈后头哭,肩膀一抽一抽的,像被雨打坏的茄子。有回她娘家爹妈来了,两个老人缩在门角,她攥着围裙直搓手,直到罗家中在堂屋里骂骂咧咧地喊”还不做饭,想饿死老子”,她才像受惊的兔子似的蹿进厨房。后来听我娘说,梁家原是和罗家差不多的人家,可她爷爷被拉了壮丁没回来,奶奶被保长占了,一家人在村里就像被踩进泥里的草,直不起腰。
罗家中的坏,是长在骨头里的。他十八岁娶了梁氏,拳头比话多,梁氏脸上的青紫旧伤叠新伤,却连哭都不敢大声。更让人脊梁发冷的是,他仗着家里有田有势,连没出五服的堂兄弟媳妇都不放过,夜里常有人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哭声,第二天见了罗家的人,都低着头绕着走。
四九年秋天,村里突然热闹起来。敲锣打鼓的声音惊飞了树上的麻雀,农会的红旗插在罗家的院墙上,分田地的红榜贴在祠堂门口,梁氏站在人群后,手绞着围裙,眼里第一次有了点光。可这光没亮够三个月,就被罗家中掐灭了。
那天清晨,他揣着把柴刀堵在村口,红着眼喊:”蒋介石就要打回来了!分了我的田、我的牛,都给我吐出来!”农会主席刚上前理论,就被他带来的几个家丁捆了,吊在祠堂的横梁上。绳子一松,人”咚”地砸在地上,腿当时就折了,后来成了瘸子。罗家中站在台阶上,唾沫星子横飞:”打倒共产党!”
没过几天,区上来了个新区长,可这人说话颠三倒四,对农会的事一问三不知。罗家中更嚣张了,居然在晒谷场上摆酒,喊着”蒋介石万岁”。直到一周后,真正的区长带着队伍进村,人们才知道,先前那个是冒牌货——他杀了上级派来的真区长,想趁机搅乱局面。
新区长是个红脸膛的军人,腰间别着匣子枪。他没多说话,当天就把罗家中一伙人抓了。公审大会开在河滩上,梁氏站在最前排,抬头看着台上被捆着的男人,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宣判的时候,风把”死刑,立即执行”几个字吹得很远,我躲在大人腿后头,看见罗家中瘫在地上,裤脚湿了一片。
枪声在山谷里响了三声,像炸雷似的。我偷偷扒开人群看过去,罗家中趴在地上,再也不能骂骂咧咧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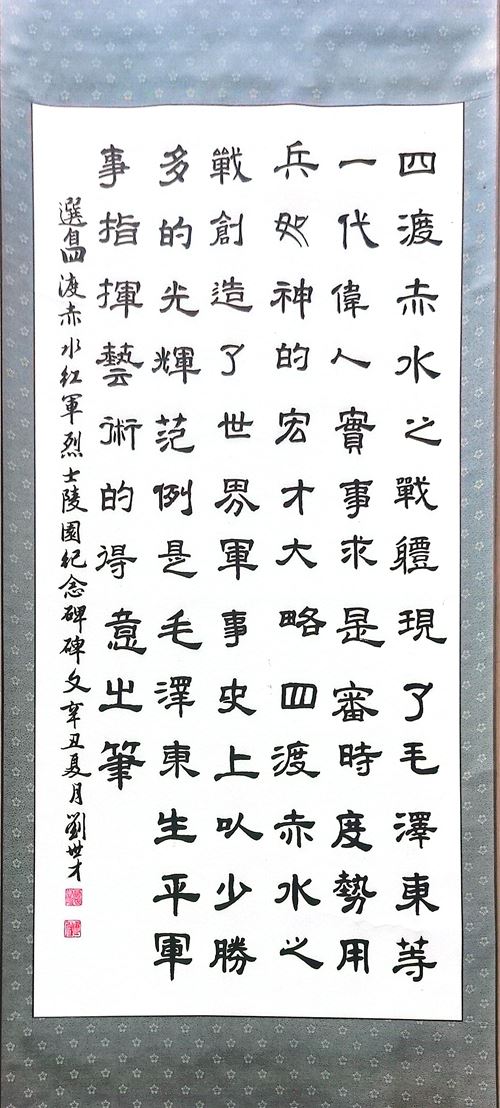
后来梁氏改了嫁,嫁给了邻村一个老实巴交的木匠。再见到她时,她脸上的青紫消了,眼睛亮堂堂的,怀里抱着个胖小子。有人说她后来又生了个儿子,两个娃都考上了大学,成了穿皮鞋的干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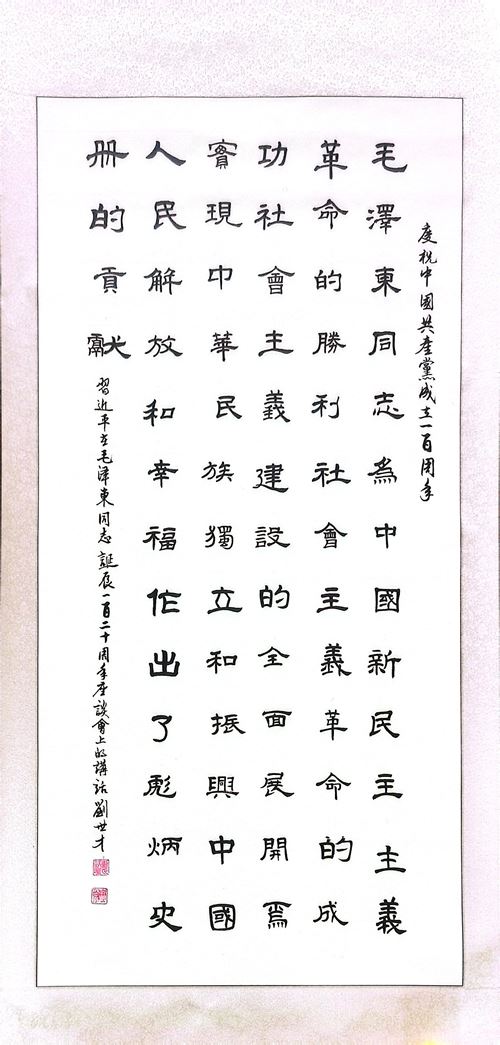
去年我回村里,老屋拆了盖新楼,祠堂的横梁还在,只是再也看不见吊人的绳子。梁氏的小儿子带着妻儿回来探亲,开着小轿车,给村里修了条水泥路。他说他娘常念叨,要不是当年那声枪响,她这辈子,怕是连眼泪都流不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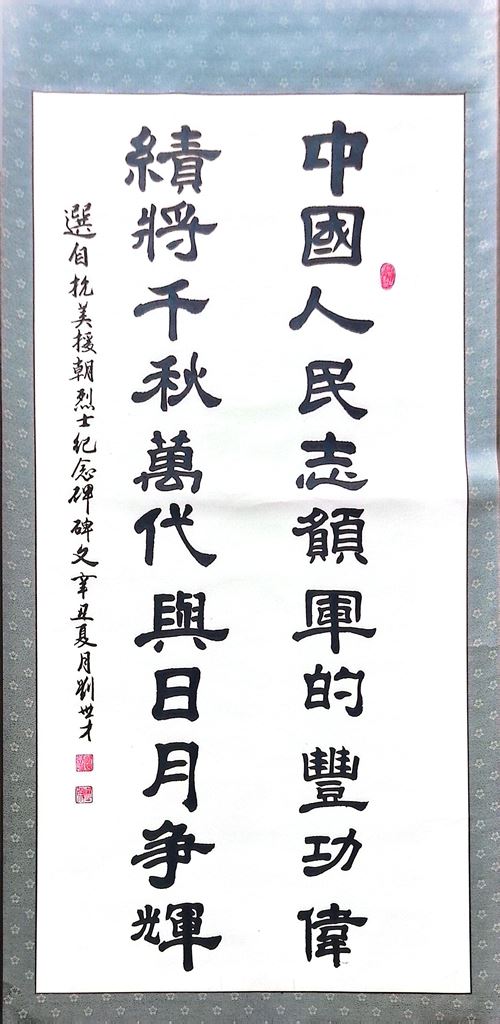
夕阳落在新修的水泥路上,亮得晃眼。远处的稻田里,谷苗和稗子分得清清楚楚,风一吹,稻浪滚滚,像在说那些过去了的,终究是过去了。
(作者:刘世才 曾经担任毛主席警卫员 编辑:魏春香 责编:韩同瑞)